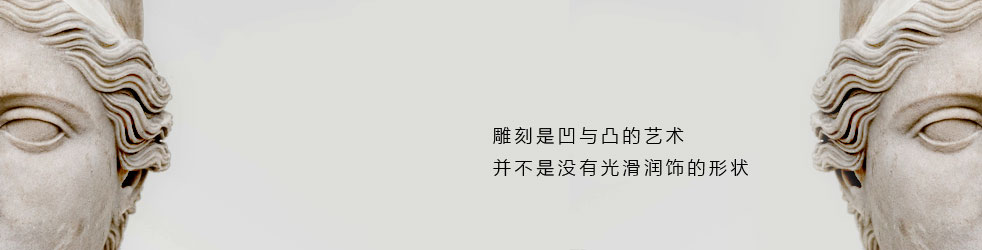
海德格尔曾用如下语言释述了艺术的本质:“由于自然苏醒了,所以它把本己的本质揭示为神圣。神圣乃自然之本质。岩石能够承载和持守,因而才成其为岩石;金属闪烁,颜料发光,声音朗朗可听,词语得以言说。所有这一切得以出现,都是由于作品把自身置回到石头的硕大和沉重的命名力量之中。”当我完成了对雕塑家赵莉的采访,面对这位看似瘦弱,但一直坚持用双手触摸石头的语言,坚持在西藏寻觅着石头魂灵的女人,我才真正理解了海德格尔话外的含义。
“我一直想做一组关于西藏的雕塑,但也许永远也找不到那种感觉。”采访时,这是赵莉惟一一句有些伤感的话语,“西藏有种悲剧的感召力。”而在我看来,习惯与坚硬石头对话的赵莉,一定想在西藏找寻那原属于石头灵魂的东西。事实上,在赵莉现在一系列的雕塑作品中,在那些石质粗犷与自由的表象下,她一直在孜孜不倦表达着对某种更为永恒的东西的追求,她一直在以石质的外壳去传达着一个艺术家对永恒的信仰与崇敬。
纳木错畔的遗憾
1996年,赵莉第一次来到了西藏。在大昭寺前,当她第一次看到虔诚的人们五体投地叩长头时,她的心被彻底震撼了。“叩长头是西藏独有的,这种惟一的信仰方式,让我在大昭寺跟在一群信众后面拍摄了整整一个星期。”正是那一次独特的摄影经历,让赵莉对西藏产生了兴趣。
2003年,赵莉来到了圣湖纳木错。纳木错地处藏北高原,是西藏第一大湖,藏语意为“天湖”。藏传佛教认为纳木错是佛母金刚亥母仰卧的化身,身语意俱全,是藏传佛教的著名圣地之一。纳木错是仅次于青海湖的全国第二大咸水湖,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湖水清澈透明。在民间传说中,纳木错是一尊女神,是念青唐古拉山神之妻。“我是清晨一大早从拉萨租车出发的。同车的还有几个老外。车开出拉萨不久,路况便糟了起来,汽车在极响的马达声中艰难地移动着。一车人在车厢里被甩来甩去。明显地感到海拔在上升了,大家的呼吸愈发困难起来,有人翻出了氧气瓶。海拔5000米的山顶,风使人透不过气来,我只觉胸口有些胀疼,一口接一口地喘着粗气。”
西藏人民历来就有“羊年转湖、马年转山、猴年转森林”的习俗。那年恰是藏历水羊年,是12年一度的“纳木错转湖”活动。赵莉到时,天已近黄昏,天空一片安详,鲜明而静寂。墨蓝的天空罩起一片弧状的雪峰,太阳就像山头上的守护神,伸手可及,一大团雪白的云朵也悄然而至。它们都被挂在山口上一串串经幡的上方。蓝、白、红、绿、黄5种经幡色布穿在几条绳索上。山风拂过,呼呼作响,阳光洒来,五彩缤纷。
赵莉仰视着被太阳照得透亮的经幡,一串神奇的光晕像五彩的珍珠,直滴在经幡上方,那一刻,她忘记了高原反应,飞快地在湖边搭好了帐篷,收拾好了行李。美丽的夕阳下,但见成千上万的“转湖”香客潮涌而来,他们转山绕湖,烧香礼拜。赵莉在野外尽情地用相机捕捉着每一个让她感动的石头的瞬间,天快黑时,她已经拍完了10多筒胶卷。
稀薄的氧气与旅程的疲惫,让赵莉一钻进睡袋便沉沉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凌晨5点过,赵莉从沉睡中被一股异样的寒冷惊醒了,耳边,阵阵大风在帐篷中犹如无人之境,咆哮而来,又咆哮而去。“高原的夜晚总是很冷的,风又大,”她刚想转头又睡,一个不祥的兆头突然闪现了出来,“不对,我记得我睡前拉好了帐篷的呀。不好!”她猛然起身,大惊失色:帐篷门户大开,“出事了!”但见帐篷里的东西一片狼藉。她急忙翻看查点:几本书和笔记还在,背包也还在角落中,食品却被洗劫一空。赵莉的心慢慢安宁下来,食品掉了倒无关紧要。但当她打开背包时,落下的心又悬了起来:她带来的胶卷与相机全没了!
第二天,有些沮丧的赵莉一个人默然坐在湖边。一个台湾的背包客走了过来,原来,他自搭的帐篷也在附近。这个从事摄影的艺术家了解了赵莉的不幸后,答应无偿给她一个尼康专业相机和10筒反转胶片,但条件是:赵莉只能使用一天。因为他带的摄影器材也有限,而任何一个艺术家都不想放弃在纳木错摄影这个难得的机会。一直使用数码相机的赵莉,拿着专业相机茫然无措。那个人又一步步教她如何使用相机,几小时后,学成的赵莉拿着高档专业相机,口袋中装着余下的9个反转胶卷,在纳木错四周开始了“疯狂”的拍摄。
天近黄昏,赵莉完成了“作业”,相机物归原主,而在纳木措遭遇打劫的赵莉,也不得不提前坐上了返回拉萨的班车。
阿里无人区的自救
每个人去西藏的原因都各不相同,赵莉的原因更为特别。在我认识的与西藏产生关联的众多艺术家中,对西藏爱得死去活来的大有其人,但赵莉是他们中间为数不多的一个深入了西藏的灵魂但又对这种深入满怀敬意的感悟者。这种敬意与感悟,让诚惶诚恐的赵莉和她手中的石头,在面对西藏时变得沉缓而慎重。“到了西藏,你才会发现‘征服自然’这个词有多么可笑。我对西藏的风光不感兴趣,那是一种轻松的东西。我到西藏不是因为它轻松,而是去寻找厚重,一种神性的有实感的东西。”赵莉说,在西藏,她最喜欢阿里,那种苍凉和原始,让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沉浸在历史之中。“这种沉浸是石质的”,她说。
1997年,赵莉孤身一人到阿里无人区采风。从札达返回巴尔兵站的途中,道路开裂了,汽油也用光了,司机对一车人说:“没办法,只有派人走路去兵站求救了。”赵莉勇敢地报了名,带上3个比他小的男子上了路。司机告诉他们,从这里到兵站,只需4~5小时的行程。
下午6点钟他们4人出发了,都带了一瓶矿泉水,两个苹果和一个手电筒。一路上,他们边走边计算着时间,合理分配着体力。大约一小时走3公里,然后休息3分钟再走。天近黄昏,望着绵延的群山,赵莉心里不停地打鼓:我们是不是在原地转圈呀?深夜,他们来到了一条冰河边,赵莉看了看表,已是第二天凌晨5点了。这时,手电筒的电也用完了。他们不敢贸然前行,在河边的一块大岩石堆下过了一宿。那是一块1.5立方米的凹形石头?熏他们4人像沙丁鱼般紧贴成一线,相互间已经感觉不到彼此的体温。冰冷的石头紧贴他们的脊背,寒冷的空气夹着淅淅小雨不停地打在4个孤立无援的寻路者身上。
第二天,趟过冰河,他们又上路了。残酷的现实,荒无人烟的恶劣环境,让同行的3位男士产生了幻觉。他们不时指着荒凉的山地对赵莉说:“快看,那里有帐篷!”但赵莉冷静地处理着一切,途中他们又趟过了两条冰河,天近黄昏时,他们蹒跚着脚步,终于看见了巴尔兵站的大门,而这时,距离他们出发的时间已有整整23个小时。
后记:阿里的诗篇
对赵莉采访结束的一个星期后,朋友给我转来了赵莉写给我的一封信。在信中,赵莉说:她不知道那天她是否传达出了某种无法言说的话语,她引了瑞士学者让·斯塔罗宾斯基的话:“被隐蔽的东西使人着迷……在遮蔽和不在场之中,有一种奇特的力量,这种力量使精神转向不可接近的东西……”她说,面对西藏,她想表达的正是此意。
在信的结尾,她摘录了自己曾经在阿里写的一段日记:“坐在古格王国对面的山脚下,我抬头仰望,轻闭双目,用心去触摸每一寸断墙残壁。夜晚的札达星光灿烂,它的魅力让我不得不用整夜的时光去漫步,用一个一个脚印去覆盖与丈量。”
我想起荷尔德林的诗句:“哪里有危险,拯救之力就在哪里生长。”也许在赵莉的西藏故事中,她会选择用一生的时光去漫步,用一块块的石头去覆盖与丈量灵魂深处传出的厚重与悠远。也许,她所追求与找寻的,就是大地的石头。
发表评论
请登录